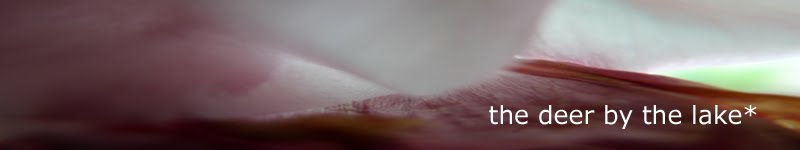香港節慶管弦樂團 節樂●黃家正 hkfo x kajeng wong
17-8-2010 @ 8:00pm @ tsuen wan town hall auditorium
死亡
不知為什麼,每次接觸黃家正,都會想起「死亡」這件事。
無論是看完《音樂人生》;聽過他的電台訪問;或出席過他的音樂會。每每如是。
我甚至,會想起一些認識而早逝的人。
黃家正那份青春,沒有匹敵。
他那份對生命的熱情,超越了對死亡的迷思想像。至少到目前為止,我這樣認為。
哭不哭
從序幕的柴可夫斯基「弦樂小夜曲」開始,我便有這個想法:為什麼非要這樣傷感不可?弦樂小夜曲的第一個小調和弦幾乎教我哭了出來。我想起艾慕杜華的電影《對她有話兒》(talk to her)裡的那個在劇院裡哭的男孩。我想起從前聽說過什麼"演的是傻、看的是痴"這說法。我想起太多東西。我想像太多事情。若果我沒有想起這一切的一切,我聽著柴可夫斯基的「弦樂小夜曲」,我會想哭嗎?
OK,不哭了,因為音樂很快移到明朗的大調。緊張的提琴和湊密的弦線與琴弓的摩擦讓我什麼也沒辦法想。
放譜
我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麼鋼琴獨奏或在鋼琴協奏曲中的鋼琴演奏者總是背譜的?因為是獨奏啊!鋼琴作伴奏時便不用背琴譜了。但這樣的答案不能教我滿意。直至黃家正,他作了一個有心思的示範。
黃家正拿著一本琴譜,走進已坐滿管弦樂團成員的舞台上,把樂譜放在鋼琴的譜架,是貝多芬的「第四鋼琴協奏曲」。然後,他說了一些很體貼的說話(真是一個嘴滑的少年)。他說他帶樂譜來演奏,是希望跟管弦樂團的所有樂手一起演奏貝多芬的音樂,不分你我(伴奏與獨奏)。然後,音樂響起。
黃家正的選曲從不深奧莫測,返而平易近人得或許會令你帶點輕視。他沒有十指飛彈的演繹,沒有作出演奏家應有的示範;手指只是工具,音樂卻說出一切。在這個時候,評論與分析或者應該暫且擱置,因為,在音樂裡,我們不需要保持清醒。
往生
「自新世界」,多麼令人嚮往的名字,彷彿見字便嗅到清新的空氣,一臉盼望。
從捷克來美的德伏扎克的第九交響曲「自新世界」第一樂章開始便能夠嗅到美國的味道,充滿美國民謠色彩,好像在看一部荷里活電影。啊!我彷彿看見里安納度•迪卡比奧!
特別想提第二樂章。第二樂章的主旋律在初級鋼琴課本裡有一個簡易的版本,但片言隻語的單音不能表達箇中的情感,就像是牙牙學語的嬰孩一般。還是第一次聽現場的原版。主旋律伴有三度和聲,豐富了聽覺,聽者彷彿置身在茫茫大海之中,被海擁抱著。聽者追著和聲,就像船追著浪。
德布西的月光
除了虛擬歌手lily chou chou*的歌聲貫穿著整部岩井俊二的《青春電幻物語》(all about lily chou-chou)外,還有德布西的音樂。德布西的音樂是怎樣的?在新潮文庫出版的《古典音樂欣賞入門》有這樣的形容:「像光影般不斷的搖動,瞬間影像的連續,這便是所謂的印象派音樂,也就是德布西的音樂。」
我知道黃家正是會再彈這一曲的,但心裡有點掙扎。我不知為什麼會這樣,但我沒有選擇。第一次是在《音樂就係咁音樂會》聽到的。我和朋友都彷彿從抽屜中找出一封舊信件一樣。是回憶的錯愕。
然而,當再一次聽黃家正彈出德布西之月光的第一個和弦那一刻,彷彿有些什麼在心裡死掉了。
再說柴可夫斯基
到底,柴可夫斯基寫「弦樂小夜曲」的時候,他有哭嗎?
我為一個合唱團彈伴奏一年多了,認識了一些俄國的合唱歌曲,每一首都好像是一支沉鬱的花朵,一種哭不出聲音來的格調。據說柴可夫斯基自小便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孩子,甚至曾因一段對錯門的婚姻企圖自殺。死亡是什麼?耶穌說死後有永生,是盼望;奧修說死亡只是一個更深的睡眠;你說呢?
*chou chou是德布西女兒claude emma的花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