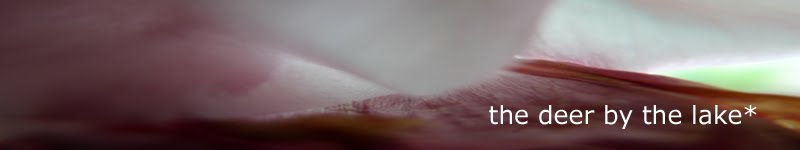週日午後,我們一家四口,大概自十年來第一次舉家前往拜祭先人。小時候跟阿嫲和當時還未結婚的阿叔一起住,每年清明節阿嫲都會帶我們前往拜祭阿爺。由於跟阿爺素未謀面,拜山給我所留下的印象和記憶就是那些煙霧迷漫的香燭和那些燃點著的元寶蠟蠋衣紙冥鈔所噴出的黑黑的濃煙佈滿整個安放了萬多個靈位的八層建築物裡。來拜祭的親人大都狀甚傷感,因為濃煙撲鼻衝眼,淚水流個不停。還清楚記得三姑姐曾取笑滿面淚水的我是不是很傷心。供奉先人的燒肉白切雞生果於拜祭後也不顧衛生的一家人照吃可也。但燒肉真的很好味。
我出生的時候阿爺已經死了很多年,對他的印象就只是在小小的墓碑上那一幅小小黑白的遺照,樣子長得不錯,而且很年青,他死時是五十五歲,但照片是他在四十多歲時拍的。阿爺的臉算是和藹,不像爸爸說的那樣是一個很兇惡嚴厲的人。爸爸一直很少提及阿爺的事,只知道他打孩子打得厲害,甚至聽聞曾經打過有了身孕的阿嫲。自從阿嫲去年過身,追問起有關阿爺和阿嫲的往事,才比較知道多一點。他們在鄉下認識,阿嫲很年青便嫁給阿爺,一直在田間工作,由於要跟其他家族成員的女人競賽插秧,捱壞了身子,傷了肺臟;後來他們生了五個男女;在我爸爸十多歲的時候舉家偷渡來香港定居,並生下幼子即我的阿叔。基本上,理髮是上一輩的家族職業,包括我阿爺,爸爸,伯父和阿叔都是吃這行飯的。除了阿叔後來跟隨我的姑丈轉行做打齋外,爸爸和伯父至今仍然在上海式理髮店當理髮師。此外,有關阿爺的事跡都令我感到時代之久遠。其實只是幾十年前發生的事,但感覺已是另一個世界。
阿爺死於癌症,臨終前骨瘦如柴,聽說離世前彷彿見到牛頭馬面般叫嚷著不要拉著我。爸爸說阿爺是鴉片煙民,當年阿爺吸鴉片煙得了癌症,便是由爸爸獨自一人背著沉重的阿爺,走過高高的樓梯,到處尋醫,可是醫生說情況已十分嚴重,要立即送院。但一切已經太遲了,最後阿爺便於還算是年青的歲數,遺下了他的妻子和六個兒女。當爸爸訴說著這些歷史的時候,阿爺在我的印象裡第一次變得立體。而且有點像粵語長片的情節。
去年阿嫲也仙遊了,年老和肺部衰竭,或者跟年青時在鄉下操勞的田間工作不無關係。而且阿嫲嗜打牌如命,六十歲時還白天上班,夜間跟鄰住的鄉友們通宵打麻雀,吃得也不健康,家鄉飯菜味濃油重,最記得鋪在湯面上那厚厚的雞湯油。
但真的真的很好吃。是最好吃的菜(現在是媽媽燒的菜最好吃)。
阿嫲和阿爺的骨灰合葬在一起,墓碑上貼上阿嫲八十歲大壽時所拍攝的照片,對照著阿爺四十多數時拍下的遺照,媽媽說好像是時光倒流一樣。
我仔細地看著阿嫲阿爺的遺照,想著,其實有緣合葬在一起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Thursday 22 March 2007
Thursday 15 March 2007
媽媽
前幾天回老家過夜,睡在硬硬的碌架床上,做了一個很可怕的夢。
我夢見媽媽死了。
夢裡我歇斯底里地痛哭,一直喊著媽媽,媽媽!就像是小時候被遺下在陌生的街道上的那種叫法。我感覺到,媽媽的死亡就是我整個人被遺棄在這個世上的嚴正開始。
夢醒的前一刻我已決定不會把這個夢境告訴媽媽,怕她會不開心。
然而,那個早上第一個看見的人便是剛下早班回來的媽媽,我連自己昨夜做夢也怕得不敢告訴她。
我只希望,媽媽在我身邊的日子越久越好。
我夢見媽媽死了。
夢裡我歇斯底里地痛哭,一直喊著媽媽,媽媽!就像是小時候被遺下在陌生的街道上的那種叫法。我感覺到,媽媽的死亡就是我整個人被遺棄在這個世上的嚴正開始。
夢醒的前一刻我已決定不會把這個夢境告訴媽媽,怕她會不開心。
然而,那個早上第一個看見的人便是剛下早班回來的媽媽,我連自己昨夜做夢也怕得不敢告訴她。
我只希望,媽媽在我身邊的日子越久越好。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