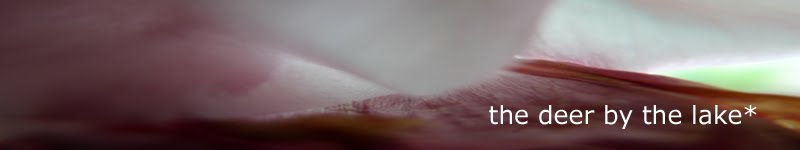作為一個曾經淺嘗教書滋味的代課老師;作為一個現職鋼琴老師,我有必要,及逼切地,將以下的種種都說出來。
一個十一歲的小學生,上鋼琴課的時候,他的身體和樣子都跟喪屍沒有兩樣。他把那雙冰冷的手伸出來,了無生氣地在琴鍵上敲出聲音。我問他:「你喜歡彈鋼琴嗎?」他翹嘴說:「不知道,一般啦!」然後我問:「那你喜歡音樂嗎?」他一樣冷冷地說:「不知道,一般啦!」
「那麼,你喜歡唱歌嗎?」
「我不唱歌的。」
「上音樂課不是要唱歌的嗎?」
「我不唱歌的,音樂都不是主科,不太要理會。」
「不是主科便不用理會嗎?」
「不是太重要,主科佔的分數比較多,老師是這樣說的。」
「那你的興趣是什麼?你喜歡什麼?」
「不知道呀。」
一個中二學生在上他第四堂鋼琴課時對我說:「老師,我還是決定不學琴了。」我問他為什麼,不喜歡嗎?還是太難?彬彬有禮的中學生說:「呀!都不是。只是,我發現原來學琴不能算在課外活動的累積分數計算之內。」
一個學生家長跟我說,他很希望他的兒子盡快完成三級鋼琴考試,因為他將來轉校的時候需要呈交有關音樂的証書。我告訴他學鋼琴不是這樣的,你的孩子其實更想學結他,不如讓他試試吧!
我想問,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否畸形了?是否都把學生和家長,甚至老師都逼瘋了,是否,我們都是為了分數而讀書、而活著?
曾在一所小學當代課老師,每天密麻麻的工作彷如揮之不去的惡夢。早會前的英文補習班、早會維持列隊秩序、一班接一班的30多40人的課堂、中午當值看守學生午膳、小息當值維持秩序、備課、批改厚積如山的作業簿、接見學生、接聽家長電話、校對考卷題目、負責課外活動、帶領學生上校車、出席各個不同議題長達數小時的會議…
Sorry,我真的受不了。試想想,我只是一個教10個星期的代課老師,我的工作量已經比正式老師為少。但,受不了的豈止我一個?在這學校那10星期短短的教職生涯裡,我看見兩名老師辭職,而每天也有老師嘮嘮叨叨及頻請病假。
教員室怨氣甚重。
為什麼老師的工作量是如斯驚人?為什麼有些老師要面對同工不同酬,導致他們覺得被剝削、不公平,教得不開心?為什麼小班教學遲遲不能落實,讓同學和老師都有一個比較理想的學習及教學環境?是2003年就 “反削教育經費,推行小班教學,資助副學士” 辯論,功能組別投下的那15張反對票嗎?是政府從來沒有重視過本土的教育政策嗎?是因為高官的孩子們都就讀國際學校或往外國升學所以便不用將資源投放在本土教育上嗎?
請給我一個答案。
我們要等到何時,才能有一個理想的環境,有一個足夠的支援背景底下,讓老師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我們的學生,讀書不是求分數,學琴不是為考級?
所以,功能組別這個絆腳石是務必要被推翻的。
所以,5月16日是一個僅有而寶貴的機會,讓我們憑自己的一票,去表達我們“受夠了”的情緒,去表達我們急切要廢除功能組別的訴求,去表達我們熱切爭取真普選的願望。
香港島的朋友,請投陳淑莊一票(政綱:盡快實現真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
九龍東的朋友,請投梁家傑一票(政綱:盡快實現真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
九龍西的朋友,請投黃毓民一票(政綱:盡快實現真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
新界東的朋友,請投梁國雄一票(政綱:盡快實現真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
新界西的朋友,請投陳偉業一票(政綱:盡快實現真普選 廢除功能組別)